值得大学生崇拜的偶像陈道明在60岁前夕静待无用之时以从容姿态迎接生活
文/陈道明 —— 在六十岁的门槛前,静心享受无用之事

一晃,我已年过花甲,这个年龄,无不提醒着身心健康的重要性。然而,将其提升到“养生”的高度,又似乎有些牵强,因为我所做的一切,只能说是“奇技淫巧以悦妇孺”。尽管如此,不做无为之事,又怎能消磨这漫长的人生?这个观念,或许与我早年的经历有关。我出生在天津一个中医世家,父亲是一位燕京大学毕业的医学家,在天津医科大学教授英语。由于家庭影响,我从小就有了成为律师、外交官或医生的理想,但这些计划都未曾付诸实践。
高中时期,由于避免上山下乡,我不得不报考了天津人艺话剧团。进入剧团后,即便没有立即成名,我也在舞台上默默耕耘了多年。那时候,演艺界还是一种吃大锅饭的生活方式,其中主角和配角的收入差异并不显著,加上自我感觉“入错了行”,对出人头地并没有太多奢望。相比之下,现在社会中的许多人接受的是一种以竞争为核心,以“你死我活”教育的心态,这让我觉得自己幸运地逃脱了一种急功近利的心理状态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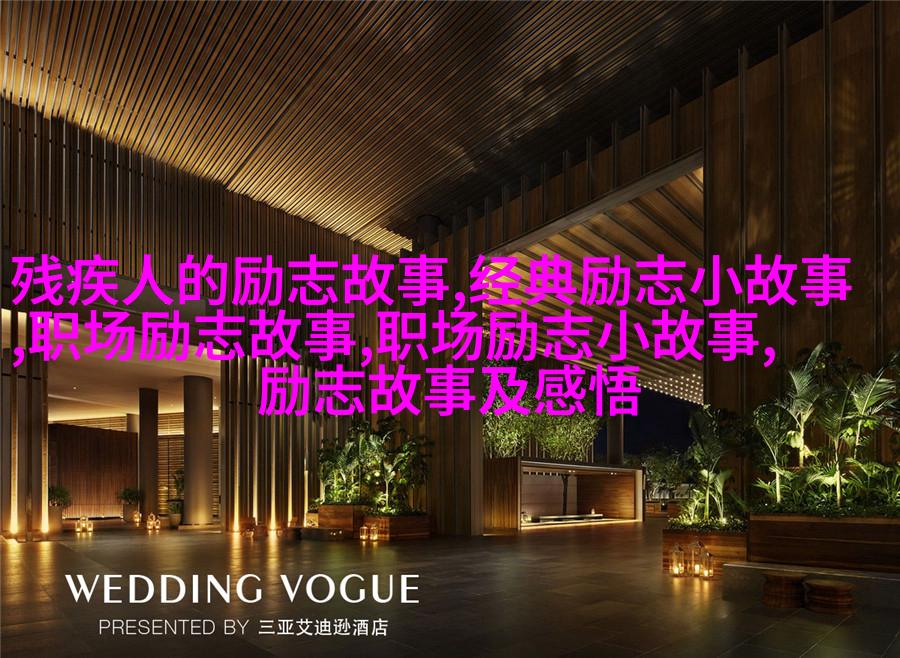
其实,不仅仅是演员,现在整个社会都似乎得了一种“有用强迫症”,崇尚一切都以“有用”为衡量标准,有用的学习,无用的抛弃……许多技能和它们原本提升自我、怡情悦性的初衷越来越远,因此社会变得越来越功利,而人们的心灵则变得越来越浮躁。但世界上的美妙往往来自于那些看似无用的物品,一场突如其来的春雨虽然无用,却能给人带来沁心脾肠的情感;刺绣和手工虽无用,却能够给我们带去美感和惊喜;诗词歌赋虽然无用,却能够触动人的心声,抚慰哀伤……老子在《道德经》中讲述:“圣人处无为之事,行不言之教。”人的生命既包括肉体,也包含精神,这两者都是不可或缺的前提。
与追求有用的东西相比,让我们静下心来,细味那些看似无用的东西带来的宁静与美好吧。安定的心灵,便是身体安康。在我的童年里,我弹钢琴得十分精通,对音乐充满热爱,每天都会花费至少两三个小时练习。我有一台珍贵电子钢琴,无论何时何地,都会携带它,并在拍戏间隙使用它,或偶尔借助剧组设备尝试其他乐器,如手风琴或萨克斯管。钢琴对于我来说,是一份私密而亲密的朋友,它让我的内心得到释放,与混乱的人际关系保持距离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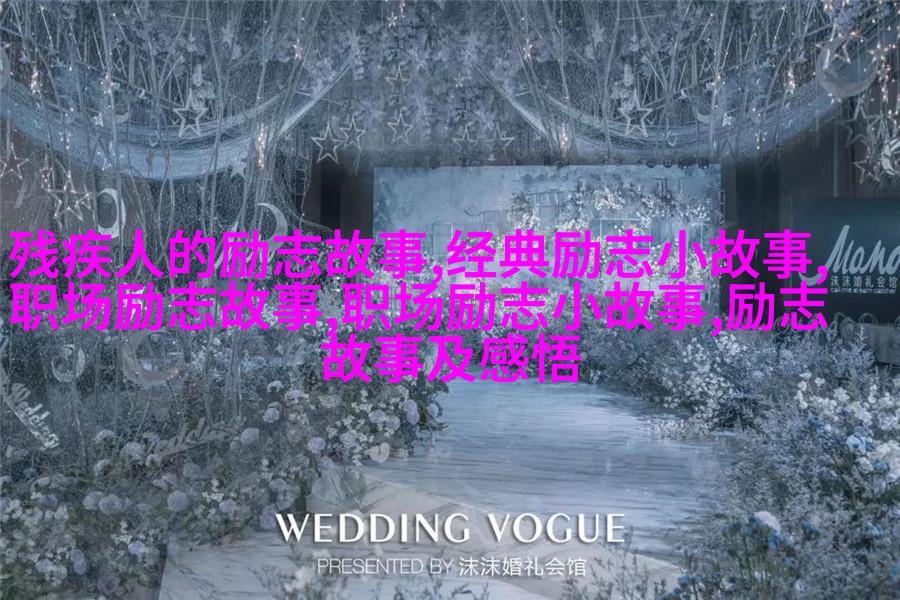
随着年龄增长,我开始迷恋画画,没有固定的艺术流派或者章法。我会磨制墨汁、铺设宣纸,然后拿起笔,在回忆拍摄旅行地点时勾勒山水景色。一旦作品完成,就贴放在书房墙壁上,用眼力比较直到感到满意才停止。这也是书画合二为一的事实之一。而后,当我发现书法也同样吸引人时,更深入其中去了。我现在最喜欢使用毛笔抄写古籍,比如《道德经》,边抄边读,使其融入脑海深处,那是一种特别愉快且富有意义的事业。
此外,还有一点钟情:棋艺。当围棋、象棋、国际象棋等各类游戏占据我的时间时,或许可以说是我什么都不不会,但实际上只喜欢独自一人下棋。在这种情况下,可以沉浸于思考宇宙奥秘,以及人类生命简短这一哲学问题。这类游戏中的策略丰富,其乐趣就在于忘却胜负,只需专注于每一步棋走向最佳结果,而非输赢本身。此外,还包括制作糖果、小木工以及裁缝工作——这些是我掌握得还算好的技能。不过,最大的梦想仍然是撰写杂文。我最尊敬的是鲁迅先生,他那样的散文给我留下极深刻印象,《鲁迅全集》几乎全部阅读完毕。在阴雨连绵的时候,如果有人问你是否愿意一个人坐下来写作,你一定会回答肯定的。但至今还未真正尝试过,因为觉得很难需要一个恰当环境和心理状态先要清洁自己的内心,没有杂念,看着窗外飘落的大雪,小棉袄轻柔包裹身体,一盏纸糊灯罩下的灯光照耀,一支烟燃烧但不吸烟,一支沉甸甸的手持笔尖蘸取墨水,为文字寻找正确的地方思虑三思,再踱五步方可决定将文字表达出来。而别人才会说你怎么还有空闲时间呢?其实,就像鲁迅说的那样,“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,只要挤总是有的。”作为一个不抽烟也不喝酒的人,从不参加社交活动,所以几乎从未踏足酒吧或歌舞厅,而且即使参加,也通常不会超过半小时。工作以外剩余时间,便是在读书练字弹奏乐器制作衣服改衣装备皮革包袋之间度日。这些可能被视作“奇技淫巧以悦妇孺”的事情远远不能比起一次聚餐更具利用价值,但正因为如此,我们才需要给自己的灵魂找到归属,让自己保持自我、本己真实。如果要谈论养生的秘密,那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了不断更新换代,使自己更加年轻。“这是养生的一般原则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