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十大杰出90后方得从容60岁前夕的无用之作
文/陈道明 ——无用之作,60岁前夕的奇技淫巧

一晃都年近六旬了,说不注意身心健康那是假的,但上升到正经八百的“养生”高度,又似乎不那么对味儿,因为我做的,用冯小刚的话说都是“奇技淫巧以悦妇孺”,不过,不做无为之事,又何以遣有涯之生? 这观念打远了说,可能与我早年的经历有关。我生在天津一个中医世家,父亲是燕京大学毕业生,后在天津医科大学教英文。受家庭影响,我少年时期的理想是当律师、外交官、医生,人生规划里完全没有“演员”。但高中时为了躲避上山下乡,有个正经的城里饭碗,不得已报考了天津人艺话剧团。进剧团后也没有一鸣惊人,多数时间都在舞台上跑龙套,一跑就是六七年。 那时候演艺界都是吃大锅饭,主角和配角的收入相差不大,加上自我感觉“入错了行”,对出人头地没有什么奢望。
其实不光演员,现在整个社会都得了“有用强迫症”,崇尚一切都以“有用”为标尺,有用学之,无用弃之……许多技能和它们原本提升自我、怡情悦性的初衷越行越远,于是社会变得越来越功利,人心变得越来越浮躁。 但这世界上许多美妙都是由无用之物带来的,一场猝不及防的春雨或许无用,却给人沁人心脾之感;刺绣和手工或许无用,却带给我们美感和惊喜;诗词歌赋或许无用,但它可以说中你的心声,抚慰你的哀伤……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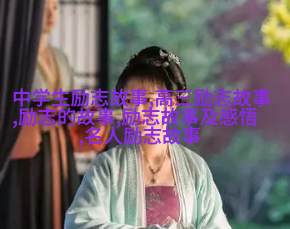
老子在《道德经》里也讲“圣人处无为之事,行不言之教”。人的生命包含肉体和精神,前者是基础,后者是升华。与其一味追求有用的东西,不如静下心来细细品味那些看似无用的生活享受,它们能够带给我们静谧与美好。
我的生活充满了这些所谓的小乐趣。我从小弹得一手好钢琴,每天都会花两三个小时弹奏。如果没法拿到真正的小提琴,我会模仿萨克斯管吹奏,或是在拍戏间隙使用电子风琴。那是一种非常私密且个人化的情感表达方式,让我能逃脱现实的一切烦恼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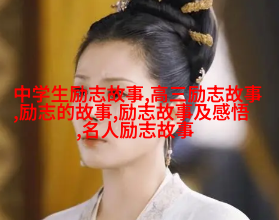
进入中年后,我迷上了画画,没有门派,只要磨好墨汁铺好宣纸,就开始挥笔泼墨创作。一边画,一边回忆拍戏中的景色,那些记忆被转化成了一幅幅山水图。这让我觉得自己又接触到了艺术,又重新找到了内心平静。
书法也是我的爱好之一。我喜欢慢慢抄写古籍,每次抄写完一次,就会反复阅读,看看是否理解透彻。这是我最喜欢的一种放松方式,它让我感到一种深刻而持久的心灵安宁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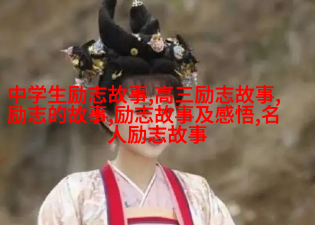
棋艺也是我的兴趣之一,从围棋到国际象棋,再到跳棋,都曾是我掌握过的手段。不过现在,我更倾向于一个人下棋,这让给我思考很多事情,比如宇宙浩瀚的人生的微小意义,以及胜败落空后的真谛。
偶尔,我还会制作一些手工艺品,如糖雕、面具或者皮质包包。在妻子的陪伴下,我们一起缝制皮革包袋,这让我们的日常充满了一份温馨与快乐。而她十字绣花草,也是我欣赏并支持的一个精致生活形式。

然而,最大的愿望还是成为一个杂文作者。我很敬佩鲁迅先生,他那种文字游戏以及智慧上的游刃有余让我深受启发。但直至今日,我仍未尝试过真正地撰写杂文,因为那需要一种纯净的心境,以及足够丰富的心灵世界去支撑这一切。如果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热情所在,并将其作为生活的一部分,那么即使工作繁忙,也总有人发现时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,即便这种活动看似毫无价值却实际上极富价值——因为它们提供的是内省与愉悦,而非金钱或者名誉。在这样的人生旅途中,我们才能保持最真实、最本真的自己,无论时代如何变化,无论社会如何变迁,这样的坚守才是永恒不可动摇的人性力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