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道明60岁前夕无用方得从容三十分钟激励短片引领自在
文/陈道明 ——无用之物,亦是养生之本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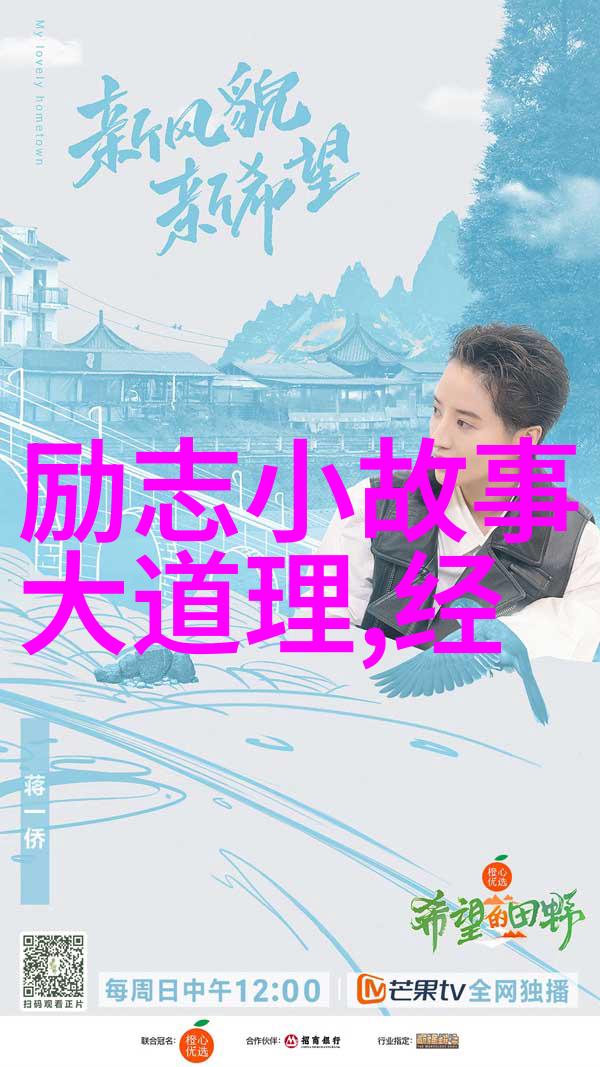
一晃,我已步入六十岁的年纪。说起身心健康,自然是必谈之事,但若将其升华为“养生”的高端话题,却似乎显得有些不伦不类。我所做的,无非是一些“奇技淫巧以悦妇孺”,不过,这样的生活,又何尝不是一种对自我生命价值的践行?这番思考,或许与我青少年时期的经历有关。在天津的一个中医世家长大,父亲曾在燕京大学毕业后,在天津医科大学教授英文。家庭环境影响下,我最初梦想成为律师、外交官或医生,但我的人生规划中,从未考虑过成为一名演员。但高中时代为了避免上山下乡,便不得不报考了天津人艺话剧团。进入剧团后,也并未立即取得成就,一直在舞台上默默奉献多年。那时候,演艺界是个大家庭,每个人的收入差异并不大,加上我自认为“入错了行”,因此对于出人头地没有太多追求。
由于起步阶段未受急功近利教育,因此很自然地学会了看淡许多事情。不像现在的演员们,他们接受的是以竞争为中心,以“你死我活”为标志的心理熏陶,使他们变得急功近利。而整个社会也染上了“有用强迫症”,崇尚一切皆以“有用”为标准,有用的学,不足者弃。这导致技能原本用于提升自我和怡情悦性的初衷越来越远,而社会变得越来越功利,人们的心灵也随之浮躁起来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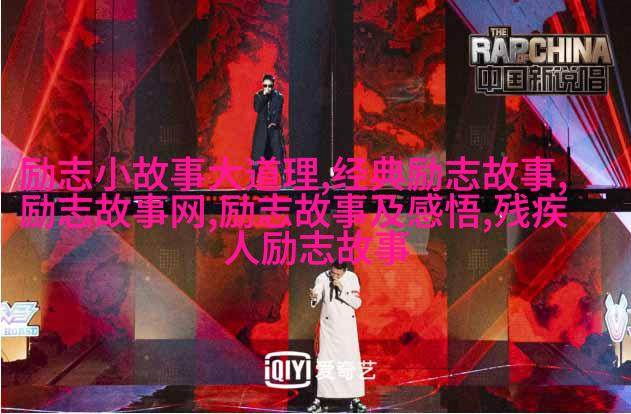
然而,这世界上许多美好的东西都是由无用的物品带来的。一场突如其来的春雨,或许无用,却能给我们带去沁心脾肺的情感;刺绣和手工虽或许无用,却能给我们带去美感和惊喜;诗词歌赋虽然或许无用,但它却能触动你的心弦,抚慰你的哀伤……老子在《道德经》中讲述:“圣人处无为之事,行不言之教。”人的生命包含肉体与精神,它们分别是基础与升华。如果一味追求有用的东西,那么静下心来享受那些看似无用的美好便会更加珍贵。心安则身安。
从小,我弹得一手好钢琴,对音乐爱到钟爱。我每天都要弹几小时,即使兴致勃勃的时候,也能持续几个小时。此外,无论何时何地,我总伴随着电子钢琴。在闲暇时光里,当遇到机会,还会尝试弹奏其他乐器,如手风琴或者萨克斯管。钢琴对我来说,是一个绝对私密且可靠的朋友,在混迹于繁忙的人群中,它成了排解内心郁结的一种方式。

进入中年之后,我开始迷恋画画,没有门派,不讲章法。我喜欢磨墨汁、铺宣纸,然后根据记忆中的拍戏地点挥笔泼墨绘制山水景色。一旦完成,便将它们贴在书房墙上,一边欣赏、一边反思,不断调整直至满意才放弃。这也符合古语所说的书画不分家之后,其实还迷上了书法,更喜欢使用毛笔抄写古籍,如《道德经》等。当抄写同时结合默读,那份深刻、那份真挚,让人觉得非常有趣。
除了这些,“棋艺”也是我的热情所向,从围棋、象棋到国际象棋,再到军棋、跳棋、斗兽棋乃至飞行棋及五子棋——几乎所有类型的手工活动都让我精通。不过,只愿独自一人下着游戏,与自己作战,因为毕竟人生的智慧如同打算盘一样,最终还是要依靠自己的双手操作决定胜负。在此过程中学到了很多关于宇宙深广和人类浅薄,以及如何通过游戏获得宁静与快乐,而忘却了输赢之间的情感纠葛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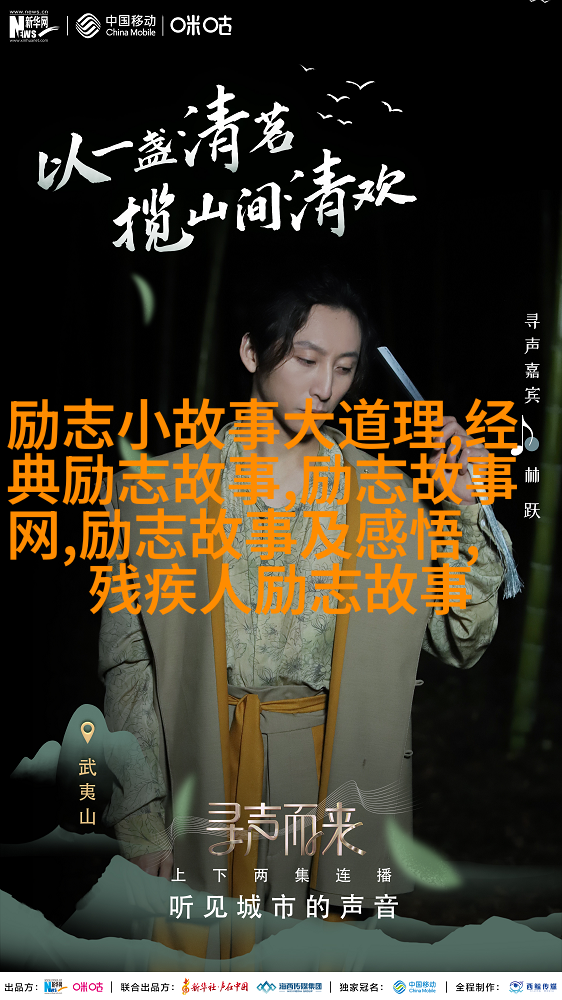
偶尔间,我也会做一些手工制作,比如糖雕面具木工裁缝等技艺,这些是我掌握得还算熟练的事情。当女儿远方,她回家的日子里,用这简单的手工作坊来表达母女间相思相念的情谊,为她制作衣裳又是一种宽慰自己心理状态的小确幸。而对于妻子的皮质包包裁缝,则更是我最享受的事务之一。她退休后,我们常坐在窗前,她织花草针线编织,而我则剪裁皮革包包设计创作。在落叶纷飞声响及温馨灯光下的共度时光,使这一切充满了一种难以言喻的情愫美感。
真正意义上的梦想,是想要当杂文作者。我最敬佩鲁迅先生,他那散漫而锋芒锐利的杂文风格给我留下极深印象,《鲁迅全集》是我阅读过最完整的一部作品。在阴雨连绵而又寒冷的时候,如果能够一个人静坐撰写文字,就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。那段时间,将自身净化,无杂念,看着飘落的大雪覆盖一切,同时身穿棉袍,上面挂着纸糊灯罩照明,一支烟燃烧但并不吸食,用沉重的手指紧握笔杆,每一次字句都经过三思五虑才能确定完善最后呈现出来。这正是在寻找那种平静而专注的心境状态,为杂文构筑基石。“时间就是海绵里的水,只要挤总是有的。”尽管生活忙碌压力巨大,但只要坚持下去,那些闲暇瞬间总能找到踪迹。而对于娱乐活动,我一直保持距离,不涉足酒吧歌舞厅这种场合,即使参加社交聚餐也不超过半小时左右。除了工作以外,大部分时间用于阅读练习书法弹奏琴曲以及亲手制作服饰装备——这些似乎都是些琐碎的小事,但它们成就了一颗独立自由而富有个人魅力的自己,让内心保持清澈纯洁,并拥有丰富多彩的人生体验。如果说有什么秘密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加年轻,那就是不断探索并坚守这一系列非凡但往往被忽视的事情:那些看似微不足道但其实蕴含力量的地方,就是让我的生命充满活力与欢笑的地方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