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名人有志气的故事陈道明六十前行方得从容之境
文/陈道明 一晃,六十之岁已临近,身心健康自当重视,但若将其提升至养生之高峰,则似乎显得过于正式。我的“养生法则”,如冯小刚所言,是些“奇技淫巧以悦妇孺”。然而,不为无为何以遣有涯之生?这念头,或许与我少年时的经历有关。我出身天津一个中医世家,父亲曾是燕京大学毕业生,在天津医科大学教授英文。家庭环境影响下,我初期理想是成为律师、外交官或医生,但人生的规划中完全缺乏“演员”这一条。但高中时代避免上山下乡,只好报考了天津人艺话剧团。入团后并未立即一鸣惊人,大部分时间都在舞台上扮演配角,一连串地跑了六七年。那时候的演艺界实行大锅饭,主角和配角收入差异不大,加上自认为“入错了行”,对成名没有多大憧憬。生活起步阶段未受急功近利教育,因此自然学会了看淡很多事物。不像现在的演员,他们接受了太多竞争为王、甚至强调“你死我活”的教育,因而心理变得急功近利。

其实,不仅限于演员,现在整个社会都染上了“有用强迫症”,崇尚一切皆以“有用”为衡量标准,有用学习,无用抛弃……许多技能原本用于提升自己、陶冶情操,却越来越远离初衷,因此社会变得越来越功利,而人心也变得越来越浮躁。但世界上的美好往往来自无用的东西。一场突如其来的春雨,或许无用,却能给人们带去沁心悦意;刺绣和手工,或许无用,却能赋予我们美感和惊喜;诗词歌赋,或许无用,但它能够触动你的心弦,抚慰你的忧伤……老子在《道德经》中说:“圣人处无为之事,行不言之教。”人的生命包括肉体和精神,其中前者是基础,后者是升华。而追求有用的东西,与其静下心来享受那些看似无用的美好,不同吗?安宁的心灵,便会伴随着身体的安康。
从小,我弹钢琴得一手好腕力。在家时,每天必弹两三个小时,当兴致勃勃时,就可能达四五个小时。我有一台珍贵电子钢琴,无论何处,都带着它。在外拍戏闲暇间,便会使用它代替钢琴,有时偶然遇到剧组设备,也会尝试吹萨克斯风。这对于我来说,是绝对私密朋友之一,在混迹于社会中,即使出现郁结,这种毫無目的的练习便成了排解内心不平衡的手段之一。

进入中年后,我迷恋上了绘画,没有门派,不讲章法。磨墨汁,将宣纸铺开,用笔画山水,然后打开地图回忆拍戏走过的地方,再挥洒墨水绘制那片景色。当作品完成,便贴在书房墙上反复观赏,对比直到满意才罢休。此外,还有人说书法与画作并不分家,所以我又开始涉猎书法领域,最喜欢使用毛笔抄写古籍,如《道德经》,边抄边默读,让知识深入脑海更添趣味。
此外,我还非常热爱棋艺,从围棋、象棋到国际象棋,再到军棋、跳棋等等,可以说几乎通晓所有。不过,只喜欢与自己的智慧较量,无论输赢全凭个人努力。在下棋过程中,可以思考宇宙深邃的人生浅薄,从而找到生命价值的一面。而且,这种沉浸式的游戏能够让我的精神世界更加丰富,为保持良好的状态提供保障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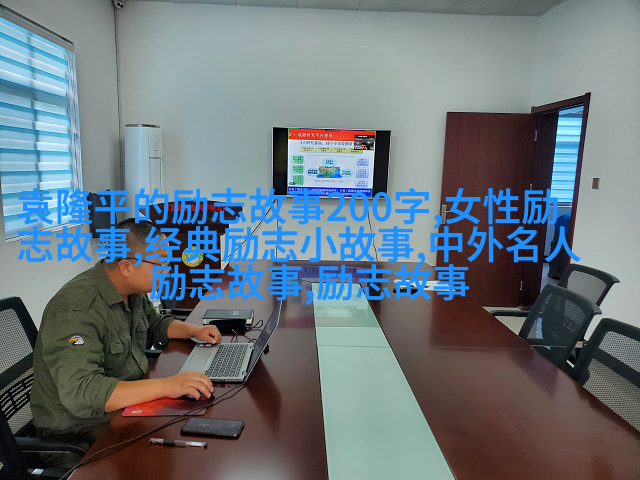
偶尔,我也做一些手工活。我家的某个房间专门存放糖娃娃、面具制作工具及木工裁缝器材,这些是我精通的小技巧。当女儿长途旅行,她常让我做点什么,以缓解思念:烹饪糖果、小塑料动物或者缝制衣服。她总是在国外,而这些简单的手工活动既让我忙碌,又让我感受到亲情与关怀。
当然,最愿意做的是帮妻子制作皮质包包。她退休之后喜欢进行十字绣工作,我们夫妻俩坐在窗边,她织花草图案,而我裁剪皮革袋子,那温馨舒适的情境,让我们共同享受一种难忘的生活乐趣。其实最大的梦想就是撰写杂文。我最佩服鲁迅,他那类文章充满智慧,《鲁迅全集》是我阅读过的一个典范。在阴雨连绵的时候,如果一个人可以静下来写作,那真是件幸福的事情。但尽管如此,我一直没有尝试,因为觉得很难,要找一个恰当的心境和环境先要洗净心灵,没有杂念,看着飘落的大雪,小声咳嗽穿着棉袄握紧沉甸甸的手提笔,一支燃烧但未吸烟、一盏纸糊灯罩下的灯光,一次次思考再三决定是否发出文字。如果有人问你忙碌啊,你怎样找到空隙呢?其实就像鲁迅说的:“时间就像是海洋里的水,只要挤总是有的。”虽然不抽烟酒,不参加社交活动,但我的时间总是不够充足,因为除了读书练字弹琴下棋,还要给女儿打衣裳给我妻子裁制皮革包装。这都是些看似琐碎却又令人愉快的事物,它们虽不足以取代一次盛宴,却让我们的日常生活增添了一份特别意义。如果把养生的秘密归纳起来,那就是通过这些方式保持内在自由,使自己的心灵永远清新而丰富——这样的人,就算活到了晚年,也依旧精力旺盛,这,就是我的秘诀。如果问如何实现健康长寿,这正是我不断变老却仍显得青涩,“奥秘”的关键所在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