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代励志人物故事60岁前夕陈道明的无用之年
文/陈道明 一晃,六十岁的年纪已经悄然降临。然而,在这个年龄,我却更加珍惜身心的健康,因为我明白,没有健康,就没有快乐。我的生活方式可能并非传统意义上的“养生”,但它源自我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事物的追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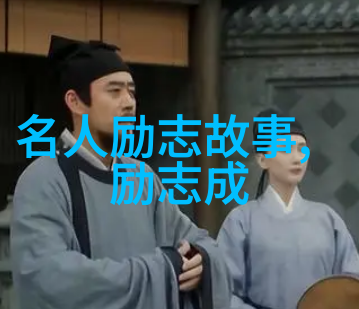
回想起我的童年,我出生在一个中医世家,父亲是燕京大学毕业生,后来在天津医科大学教授英文。我从小就被灌输了成为律师、外交官或医生的理想,但高中时为了避免上山下乡,我不得不报考了天津人艺话剧团。那时候,我并没有立即获得成功,只是在舞台上默默奉献了六七年的时间。
那个时代演艺界是集体主义为主,每个人的收入差异不大,而且我自己也感觉好像误入了一条错误的道路,所以对于有所成就并不奢望。相比之下,现在的社会似乎更注重竞争和结果,有用与否成了衡量一切的事物。而这让我感到有些落寞,因为那些曾经让人宁静感受的小事,如春雨中的沁心悦意,或许在现代被视为无用而被忽略。

然而,这世界上许多美妙的事情都是由看似无用的东西带来的。一场突如其来的春雨,无论其实际用途如何,都能给人以慰藉;刺绣和手工艺品,它们虽然不是必需品,却能够带来情感上的满足;诗词歌赋,它们虽然无法直接解决问题,却能够触动人的心灵。
作为一名演员,我有一段很长时间弹钢琴的情节,不仅因为喜欢,也因为它是一种放松自己的方式。在外工作期间,即使没有钢琴,也会随身携带电子钢琴,以此代替。这种私密的朋友,让我在忙碌的人生中找到片刻安宁。

进入中年后,我开始画画,并且迷上了书法。这两项技能让我得以沉浸于古籍之中,与自然交流。我还热衷于各种棋类游戏,从围棋到跳棋,每一种都让我领悟到生命与策略之间微妙联系。
偶尔,当思念远方女儿时,我会做一些手工艺,比如糖人、面具或裁缝活,这些活动既是一种自我宽慰,又是我表达关怀的一种方式。而最重要的是,为妻子缝制皮质包包,这份劳动给我提供了一种亲近她的机会,同时也是我们共同享受时光的一部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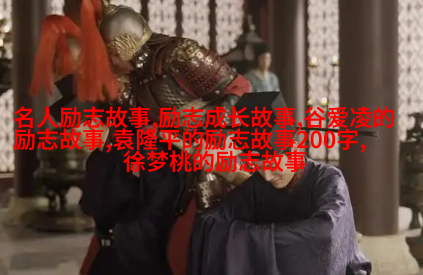
真正地,那最大的梦想,就是写作——尤其是杂文。我深爱鲁迅先生,他那种清醒而深刻的话语总能激励我。但直至现在,还未尝试过写作,因为觉得那需要一种特殊的心境和环境。但每当阴雨绵密的时候,一盏纸糊灯罩下的灯光、一支未点燃的手持香烟、一本笔记本,便是我创造杂文的地方,而这些都是帮助我排解内心烦恼的一种方法。不论外界多么喧嚣,只要有这样的空间,就可以找到安静思考,用笔墨记录下来,将纷繁复杂的心理状态转化为文字,从而保持精神世界的纯净与丰富性。如果说养生的秘诀是什么,那就是通过不断地追求,无论何时何地,都能保持一颗年轻的心靈,即便身体再老,精神依旧充满活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