活到何年才能不顾生死史铁生的成长轨迹
我常有这样的感觉:死神就坐在门外的过道里,坐在幽暗处,凡人看不到的地方,一夜一夜耐心地等我。不知什么时候它就会站起来。对我说:嘿,走吧。我想那必是不由分说。但不管是什么时候,我想我大概仍会觉得有些仓促,但不会犹豫,不会拖延。 “轻轻地我走了,正如我轻轻地来”——这句诗未必牵涉生死,但在我看,却是对生死最恰当的态度。

陈村有一回对我说:人是一点一点死去的,先是这儿,再是那儿,一步一步终于完成。他说得很平静,我漫不经心地附和,我们都已经活得不那么在意死了。这就是说,我正在轻轻地走,灵魂正在离开这个残损不堪的躯壳,一步步告别着这个世界。
比如想起清晨、晌午和傍晚变幻的阳光,想起一方蓝天,一个安静的小院,一团扑面而来的柔和的风……不知道别人是否也会像我一样,由衷地惊讶:往日呢?往日的一切都到哪儿去了?

生命的开端最是玄妙,比如出生于北京的一个普通四合院。我站在炕上,看着窗外,那时天降大雪。一天一宿罕见的大雪,使路都埋了。奶奶抱着为我准备的铺盖趟着雪走到医院,在产房窗檐下站了一宿,最终听见我的声音从无中来。在母亲眼中,“你来了”。
蹒跚地走出屋门,我进入了一个真实世界。一片花草气味、一片砖石气味、阳光在风中舞蹈流动。青砖甬道连接四面的房屋,把院子隔成四块均等土地,每块上有一棵枣树或西蕃莲。西蕃莲开硕大的花朵蜜蜂飞入飞出;蝴蝶悠闲飘逸;枣树下落满移动影子、细碎枣花覆盖在地上的青苔;远处,有些声音,有些缥缈不知所在的声音——风声?铃声?还是歌声?

迈过高高门槛,我艰难走出院门,看见安静的小街两三个陌生的身影慢慢行进,或东边朝阳,或西边落日弄花他们眼睛,他们闭上眼睛有点怕,不知所措,然后睁开又好了,便继续眺望。
那些情景,如今都到了哪里去了?那时刻,那孩子,那样的心情,都到了哪里去了?它们飘进了宇宙,是呀,它们依然存在吗?

梦是什么?回忆,是怎么一回事?倘若有一架足够大的望远镜,可以看到一切依然如此。如果那个孩子永远痴迷眺望,他便永远站在小街上。如果停下来,就重现五十年的历史,从头开始演绎。
时间限制我们,我们习惯限制我们,让我们陷于实际之中。而白昼是一种魔法,让僵硬规则畅行无阻,将奇迹消磨掉。我盼望夜晚,因为只有黑夜自由,没有预设程序束缚,只有寂静中的自由可以追求,即使是在死亡之中,也要站出来观察生活与死亡之间真正的情感流转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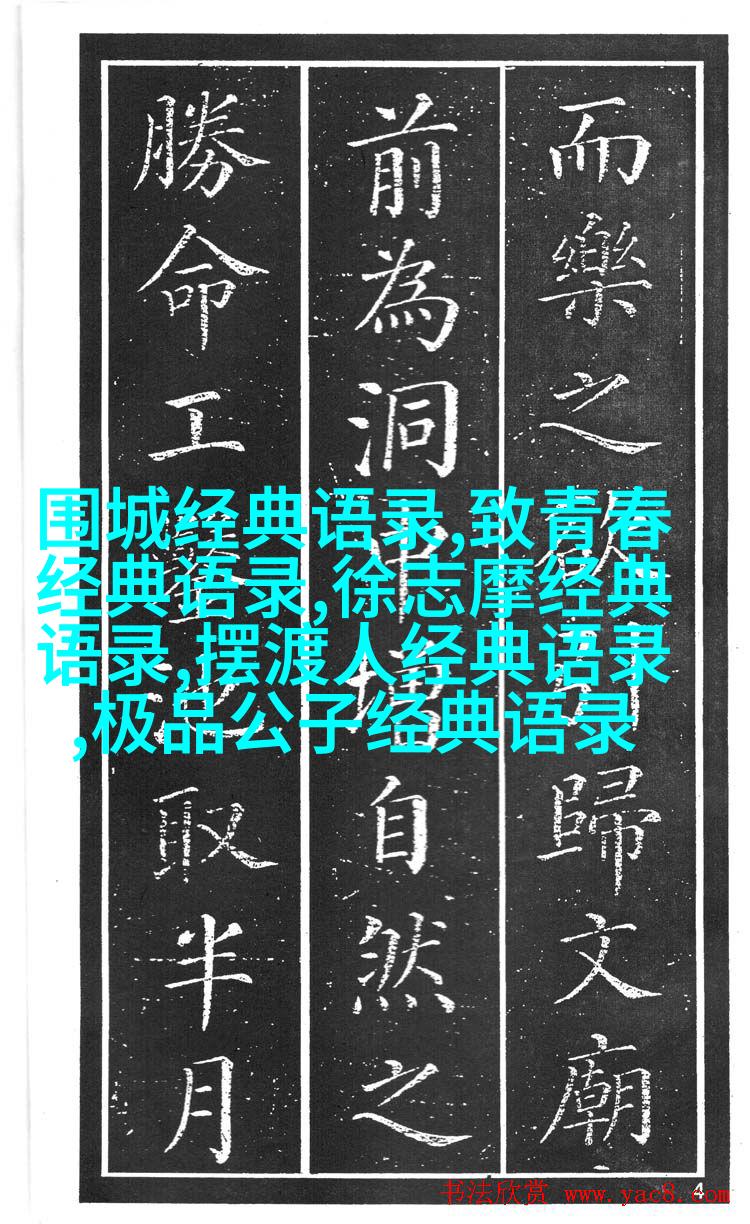
我的身体早已固定,但我的心灵常在黑夜游逛,与所有梦者共鸣,与所有放弃尘世角色的游魂同乐。在沉睡窗口传递消息,从沉睡窗口探寻被忽略的心情,这才是我想要写作的事情,而不是文学。这份自由,是写作带给我的最大快乐之一,也是我向往的人生态度。